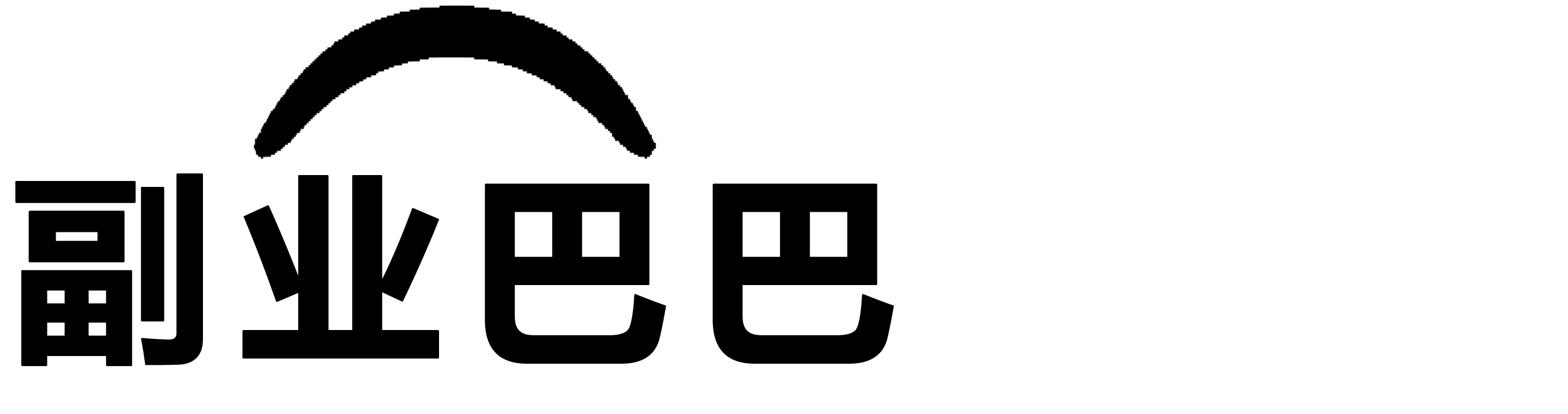那些犯了相对轻微罪行的人,由于法庭指派的律师不够充分,陪审员又不是他们的同辈,所以被关进了监狱。他们面临很多不利条件,而且他们面临着来自暴力囚犯的极大威胁。

那些在社会或监狱中都无法取得成功的人。他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?在经历了太多类似的失误之后,周围的人不再同情他们。
那些在长期服刑后获得假释但无法重新融入社会的人。尽管他们可能讨厌监狱的日常生活,但这些囚犯已经习惯了僵硬的制度结构,无法适应更大的自由。如果他们在社区里声名狼藉,那么很少有邻居会相信他们是曾经被定罪的重罪犯。
可悲的是,即使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送进精神病院,他们也无法保证上述一切。我在这里为您列出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情况。如果一切顺利,这就是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。我为上面的囚犯感到难过,但我为那些不会从上面的事情中受益的囚犯感到更难过。
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囚犯有一种奇怪的同情。
一开始是针对那些面临死刑的人,但当我开始更多地了解监狱系统后,也开始关注下级囚犯。
据我回忆,我第一次听说死刑之类的事情是当我和母亲住在第二间公寓的时候......那应该是 1997-1998 年,因为我们只在那里住了一年。
我当时正在电视上看一部老牛仔电影,不知怎么的,谈话中我的母亲随口提到,在德克萨斯州“如果你杀了人,他们也会杀了你”。
我的回答最终大致是“如果他们说对不起怎么办?”或“他们会有第二次机会吗?”等等。
几个月后,电视上播出了一场国家处决,画面中一个秃头男子阴沉地走在两排观众之间,背景中响起鼓声,我的祖父或多或少说了一句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?他们要杀了他”。
那时我没有任何我记得的可辨别的情绪,因为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仍然很新,我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。
此后不久,又发生了另一起案件,一名黑人青少年杀害了另一名学生,在宣判前询问法官是否会允许他回家——他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,不得假释。
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,强忍着泪水,想知道这个愿望被拒绝的感觉是什么样的,即使这是他自己对别人造成的——受害者的亲属事先接受了采访。
事实上,这种情感变得非常强烈,以至于在晚上,我敢发誓我看到他走上我祖父母的楼梯,感谢我把他带出来——我以前的卧室就在眼前。